|
|

来源:中国艺术鉴赏网北京
作者:江柏安 著名音乐教育家、武汉大学教授

编者:江柏安,著名音乐教育家,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。曾被评为“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工作者”、武汉大学“学生最喜爱的十佳教师”,武汉大学“杰出教学贡献校长奖”、武汉大学教学名师等,出版国家级学术著作七部。现为中国艺术鉴赏网学术顾问、武汉大学弘毅学堂博雅导师,湖北省音协“音乐爱好者联盟”主任等。本文系作者在《长江论坛》上的演讲稿。
中篇
(接上篇)在19世纪浪漫乐派那里,情况发生了变化,犹如一棵树晃动另一棵树,那时的作曲家非常热衷于为音乐加注标题,为寻求听众理解,专门为音乐作品设计文案,有时甚至不惜文学泼墨般地用语言将音乐的表现描述到栩栩如生。
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,那就是恐惧于失去听众,否则将活不下去呀。
客观地说,在当时,他们这样做还是有效果的。
那个时期的听众很单纯,不那么“开化”,往好听里说叫做尊重艺术,往难听里说叫做好糊弄,毕竟在当时,音乐欣赏还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获得的稀有资源,人们对音乐表现出的热爱,使他们还是比较容易被左右的。
可是如今,“电”所象征的现代性颠覆和还原了一切。从黑胶唱片到盒式磁带,从CD唱片到MP3,还有广播电视无线电到网络传输,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完全改变了人们对待艺术的姿态。“就是听不懂”,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简单尝试着听纯音乐而又无感之后,最直白的表达。
多元化音乐生活的景况,实际上又将大多数头脑简单的“爱乐者”单一维度地固化在了流行歌曲的低吟浅唱之中,这,成为了人们远离器乐曲音乐欣赏的标准答案。
音乐的标题或是解说文案,也不能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吗?
答案是:不能。
如前所述,我国历朝历代文化史上,那些用文字将音乐描述得天花乱坠,以图换取人们崇尚音乐的尝试,于后人而言,也大多是徒劳无益的。
所以,20世纪初,当欧洲古典音乐殿堂般的文化构造开始轰然解体,那时的音乐家就已经开始指出问题的端倪,并且拿浪漫乐派音乐标题有一出没一出地开玩笑了。法国作曲家萨蒂宣称的“像患牙疼的夜莺那样歌唱”,就是一个挺有名的例子。
那么,怎样解决人们欣赏纯音乐时关于理解的问题呢?
其实,就纯音乐欣赏而言,那原本就不是让人听懂,而是让人感受的,这是一个朴实的认知,我们只需清晰地传达给人们,顺便告诉人们,“以听懂音乐为目的,那是比较不开化的一种认知诉求”,也就行了。
可是以往,我们的祖祖辈辈好像并不情愿这么做,好像这么做了就显不出自己的高级一样,所以,在过往的生活中,像《琵琶行》那样的关于听懂音乐的文学性描述比比皆是,共同的特征是,它们非常不真实,却都高高在上,并构建出一种强大的鄙视链,拉开了与普通人的距离,这实在是令人抓狂。
那好,我们先来啰嗦一下,回答“纯音乐”是不可能听懂的问题:音乐使用的材料,是时间和声音,这两件东西都是抽象的,与概念无关,因此实难构成所谓的概念表达,比如,你就不可能用音符描绘出一个梨子的外形,贝多芬也不行,谁都不行。
实情就是这样,除了涉及抽象的情感体验,音乐什么也不能表现,既然这是真理,那放置于音乐全领域,当然就合理地支持了“音乐是最抽象而浪漫的艺术”的主张。
19世纪德国著名音乐学者汉斯·力克情急之下曾说过,音乐只有纯音乐的意义,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,“音乐就是乐音在时间中的运动”。他的意思是说,你只需要去听就是了。
20世纪初,美国伟大的音乐家艾伦·科普兰,也曾在他的小册子《怎样欣赏音乐》中吐槽说,人们抱怨听不懂音乐,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认知储备不多,而是他们心思单纯地认真倾听音乐太少。
而我怀疑的是,他们二位可能早就注意到,很多人声称自己是爱音乐的,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聪明,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地倾听音乐本身,而是在音乐之外的一些方向,比如标题或是歌词引发的想象与联想中,耗散了音乐审美的意义与价值。
因而,针对生活中人们听不懂纯音乐的表达,我常常建议大家认同下面这三句话:纯音乐是不可能听懂的;也没必要听懂;如果能够听懂,那就没意思了。
我以我音乐专业工作者的身份向大家坦诚说明,我也听不懂。
我的看法是,反正大家都是听不懂的,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,只要去听就好了,听着听着就喜欢了,属于你个人的审美也就完成了,享受生活的目标也就达成了。何况,就算是认真听了,可还是无感,那也很正常啊,你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美好都与自己有关联,不属于自己的好的东西多得去了,而总有一些好的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,你需要的就是 “努力找到它”,这才是明智的认知判断啊。
其实听得懂与不可听懂,往宽泛里讲,不过是一个哲学思辨,智者会说,听得多了,好像也就听懂了,只是这种所谓的懂,套用禅宗的话来讲,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,音乐之美就是这样,让你心动,却让你“莫名其妙,妙且难言”,还使你越来越喜欢,以致一生一世永不负心。
至于你的生活中不时会有那么一些人突然冒出来,向你言之凿凿“听懂了”,面上,你应该与之同乐,私下,你也要坚守这个主张:那不是音乐的真实,而只是爱乐者常有的尊重与喜爱,且与你关系不大。因为,音乐欣赏,归根结底是一种个性特出的行为,其感受无法复制。
1877年,俄罗斯大文豪列夫·托尔斯泰,听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《D大调弦乐四重奏》第二乐章《如歌的行板》后,泪眼巴巴地喃喃自语,“我听到了我们俄罗斯的苦难”……第一,多数情况下,这种传播是害怕你不爱乐,但你又不容易怀疑这事,你就信以为真了呗;第二,你肯定听不到“俄罗斯的苦难”;第三,这件事与你怎样欣赏《如歌的行板》无关。
综上所述,围绕“我们生活中的音乐”这个话题,我们说到了歌曲,我们比较鄙视“听歌听词”,建议大家保持“听歌听曲”的好习惯;我们说到了器乐曲,我们以纯音乐的思维判断来强调和凸显其艺术价值,倡导大家将听赏器乐作品最大限度地纳入到自己的音乐生活,不要过分地以狭隘的“听懂”钳制了音乐审美的本真,并特别指出以“关注音乐之本身”为心智模式,建立自己高格调生活与雅致文化品位。
总的说来,歌曲,继续听,乐曲,不能少,这样就好。
可是,音乐欣赏除了关注音乐之本身,除了不要拘泥于所谓听懂,除了不要沉溺于歌词不要迷失于标题,难道就没有一些有用的经验性的东西可以分享吗?
通常,我会用“什么也代替不了倾听音乐”去敷衍这个问题,因为没有倾听就没有一切,还因为,如果要观念专业地解决这个问题,那会出现好几本书的学问要去研习,势必调动一整套体系,去运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,不是说专业性不好,而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爱乐者而言,实在没有这个必要。
但是,最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,我个人还是有一点经验可以分享与大家的。
我很早就注意到,其实就纯音乐而言,所有的音乐无外乎就是“好听的声音、有趣的声音、有意味的声音”,所谓三种声音。
不管听什么音乐作品,纯粹客观地来思考我们听觉的反应和感受,在调用参考材料受局限的情况下,从“三种声音”的角度展开我们的认知,是最安全有效的。
而作为爱乐者,如果我们认同“音乐是偏向于形式美的艺术”,如果我们理解“音乐无所谓内容,音乐的内容就是音乐的形式”这种表述的含义,特别重要的是,如果我们可以注意到,在“以听觉的方式构建情感表达”的问题上,音乐只可能触及人的听觉在“基本情感层面”,亦即“一般性喜怒哀乐”的意义上,形成某些情感反应或是判断,而在“具体情感”抑或是“社会情感”方面,那将是十分勉为其难的……如此这般的话,从“三种声音”立场去听音乐,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困惑。
通常情况下,我们真心喜爱音乐,并将欣赏音乐视为享受生活,这既是生命本能,又是个人精神成长一以贯之的审美需求。
注意到这一点,所有创造音乐的人,那些作曲家、演奏家、演唱家们,在凝聚了他们聪明才智的作品中,全神贯注的首先都是听觉感官上的直觉性的好听,而一般来讲,这些好听的声音,欣赏者是很容易从听觉形式上体会到它们,识别出它们的。
只不过使人为难的是,这美感是怎样形成的?实在很难找到恒定的量化指标体系,所以我们习惯将“美”与“真”视为两类不同的问题,而且我们知道,构建声音之美的形式样态以及它们的组合与变化,是怎样刺激触发了欣赏者相对一致的共同感受,那只有一个解释:长期的积累形成的审美经验。
以下,我随便列举的音乐名作,在构成人们印象中好听的问题上,它们几乎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:著名的轻音乐团,曼陀瓦尼乐团演奏的《绿袖子》;欧洲浪漫乐派先驱,德国作曲家舒曼的钢琴套曲,《童年情景》中独霸了后世冠名权的《梦幻曲》;被誉为钢琴诗人的作曲家肖邦的《降E大调夜曲》;还有在我国一曲成名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中的《爱情主题》,那个受越剧腔调影响写成的有着明显的起伏和宽阔的音区,但就是很好听的调调;还有我国广东音乐的代表作《彩云追月》……多如牛毛,而你们应该提醒我停下来。
我们在音乐欣赏中注意到,好听的声音还经常伴随有丰富的审美趣味,这种比较高级了一点的感觉,是音乐家们特别愿意展现给听众的。
所以,有趣的声音,是音乐欣赏最值得光顾的美妙的领域。
这里能够为人所知的东西,叫才华。
音乐欣赏使人着迷,除了感官享受,最令人感动的就在于每每与才华共处。
贝多芬c小调第五号交响曲第一乐章,在结构认知的引领下欣赏到它的再现部,对一般的爱乐者都不算艰难,接下去,贝多芬突然异军突起般地又对他的主要音乐材料,也就是“三短一长”的命运动机,进行了一次展开部规模的音乐掀泻,使这个乐章高潮迭起,其构成的听觉审美趣味,给所有喜爱它的听众,足以形成强大的听觉冲击力。熟悉这个作品的人们,无不认为这个乐章最有艺术趣味、最显艺术才华、最有艺术价值的部分就在这里。(待续)
中国艺术鉴赏网各官网平台信息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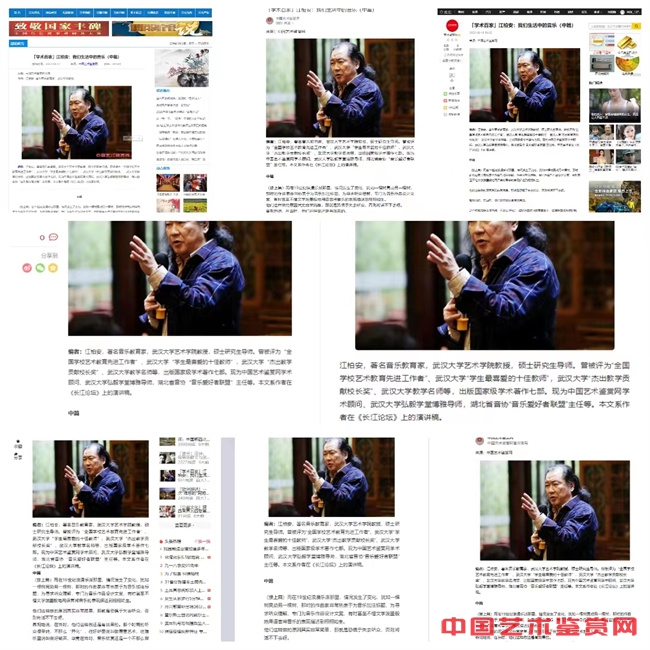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刘梅(北京)
